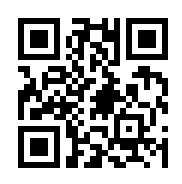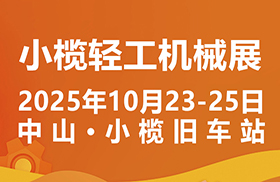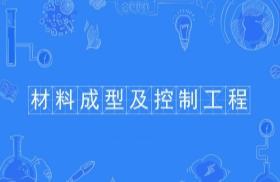在東莞,“機器換人”其實早就開始了。大朗從2008年起掀起的數控織機潮就是其中典型。2009年底,大朗數控織機不足一萬臺,經過幾年的推廣,如今數控織機使用量已超過4萬臺,共節省人力20萬人。
租賃經濟是東莞基層村組發展一個較為普遍的模式。就在東莞機器換人如火如荼地吹響號角之時,基層卻在擔憂:如果企業都用機器把人換走了,村組社區的房子租給誰住?對此,東莞市機器人技術協會副會長羅百輝表示,機器換人將是一個長期、漸進的過程,其中并不意味著企業大規模減員,甚至還會催生新的就業創富機會,成為基層經濟轉型的一個機遇。更重要的是,單靠廉價勞動力和吃租分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,機器換人與村組經濟轉型都時不我待,其中或許會有陣痛,但腳步一刻也不能遲疑。
羅百輝明確指出,機器換人是東莞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。機器換人將促進產業升級和人的升級,從而推動東莞整個城市的升級。只是在這個過程中,伴生的社會問題需要未雨綢繆。政府在大力推動機器換人的同時,還要運用好和完善配套政策,進一步激發基層創新、創業、創富的激情,破除路徑依賴,助推東莞成功轉型升級。
人機的升級
機器換人不僅可以解放更多勞動力,還可以創造更多新的、附加值更高的崗位,如機器維修、研發、銷售、培訓等,這將促進東莞產業和工人同步升級。
38歲的陜西漢子戴朝智,看護著一人多高的自動包裝機,機械手臂靈巧地將一摞重達幾十斤的瓷磚打包,由碼垛打托機器人壘起來,工友開動叉車將其運走偌大的車間里只有不到20名工人在看管機器。
東莞唯美陶瓷制造車間里,這樣的一幕近日被媒體廣泛報道。不久前,市委副書記、市長袁寶成曾在此做機器換人專題調研。
這樣的現代化工廠,與我國制造業留給人們的刻板印象似乎毫無關系。在東莞大多數工廠里,通常能見到成百上千名工人在流水線上埋頭苦干。唯美陶瓷制造車間里,也曾經人滿為患,兩三百工人在車間里人工磨邊拋光、撿磚打托。
變化發生在戴朝智被當做重勞力招進的2007年。當時,唯美陶瓷董事長黃建平出國考察后,從國外購買自動化設備,前前后后花了2億多元,階段性完成機器換人的生產轉型,節約用工2200人。
推行自動化的時候,工人中存在不同的聲音,有的擔心文化低學不會,有的怕被機器取代了。公司人力資源部門明確傳達了廠里的意思:愿干體力活,有新廠和生產線可以安排崗位;愿意轉型看機器,可以到唯美學校學習,簡單、包會。唯美東莞廠區機器換人,做到了減員不裁員。
戴朝智和幾個年輕的工友一起決定學操作機器。培訓人員把操作規則都編成口訣,讓他們熟讀并實踐,還不忘貼在機器上以供忘記時一看就會,出現問題按鈴報告。
戴朝智清楚地感受到,轉型后的工作輕松、體面:月薪從原來的3000多元漲到現在4000多元,加把勁還能上到5000元。新成長起來的產業工人,成了機器換人過程中最直接的受益者。
戴朝智的經歷,只是東莞機器換人大潮中的一個縮影。機器換人直接帶來的是城市人口素質的一次大提升。
機器設定一個程序,調節、維修等,也都是要人的。這些新崗位勞動者要具備一定的技能和文化知識,簡而言之,就是把簡單加工型的勞動者,變成技能技術型人才,即高端藍領,這正是我們需要的。厚街當前正在積極推進機器換人,該鎮黨委書記萬卓培表示,以產業發展規律來看,使用新機器、新技術時,直接操作工人會減少,但研發、銷售、服務、培訓部門的就業機會就會增加,對東莞而言,實現了產業升級與人的升級同步。隨著人的升級,收入的增加,也會為當地消費作出更多貢獻,對社會的轉型升級發揮良性促進作用。
催生新業態
大朗推廣數控織機過程中,從事數控織機生產、銷售以及售后服務的企業或機構等形成了數控織機一條街,并帶來了巨大的財富。
在東莞,機器換人其實早就開始了。大朗從2008年起掀起的數控織機潮就是其中典型。2009年底,大朗數控織機不足一萬臺,經過幾年的推廣,如今數控織機使用量已超過4萬臺,共節省人力20萬人。
大朗鎮的繁榮并沒有因此有絲毫減退。一般來說,一臺數控織機能頂6-8個人,一開始我們也擔心:換人會不會使房租減少?要知道,巷頭村80%的集體收入來自于物業出租。后來才發現,這個擔心是多余的,你看看外面的商鋪,哪一個是空的。素有天下毛織第一村的巷頭社區居委會里,負責企業工廠的村委委員陳暖根說。
巷頭居委會門外的大街上,兩排商鋪前車水馬龍。今年41歲的劉傳富租了其中的一間商鋪。以前用人工手搖機拉拉扯扯,一天只能生產四五件,現在一個人就可以看6-8臺機,一天下來可以生產200多件,而且還沒以前那么累。從工人變成老板的劉傳富說。
2002年,劉傳富從安徽到大朗巷頭村,從雜工做起,十年間做到了工廠一個部門主管,工資也從每月450元漲到了6000元。這時,工廠里已經開始用數控織機,換下來的人,大多進入縫盤、后整等工序,這些工序正缺人手。
還有不少比劉傳富更老資格的工友們,紛紛離廠單干:他們往往三五個人,湊點錢,買下十幾臺數控織機,租一個鋪位,接大廠的訂單做毛織加工。
發不了大財,但自己當老板,總比給別人打工強。2012年,動了心思的劉傳富拿打工攢的十幾萬塊錢和親朋好友的借款,買了幾臺數控織機。親朋好友全上陣,一年多下來,他的這個小作坊一年的人均收入比打工時翻了一番。現在買機器按揭的尾款差不多要還完了,之后就是凈賺的了。劉傳富盤算著在東莞買一套房子安家,他很慶幸這些數控織機讓他創業。
值得一提的是,數控織機熱也催生了另一種產業。驅車徜徉在平坦寬闊的銀朗大道,道路兩旁琳瑯滿目、鱗次櫛比的數控織機大招牌依然分外搶眼,這里已成為華南地區數控織機的集散地。
躋身其中的金龍公司總經理周齊說,高峰期時這里有一百多家從事數控織機生產、銷售以及售后服務的企業或機構,大朗銀朗路數控織機一條街應運而生,短短幾年就造就了數十名百萬富翁。金龍在2012年在華南地區的收入超過一個億,其中多數來自大朗。
大朗巷頭的故事,印證了機器換人給基層經濟帶來了更大的活力。事實上,租賃經濟絕不是東莞村組經濟發展的唯一選擇。鳳崗鎮雁田早在1988年就成立公司進行投資,近年來甚至走出東莞開展了多元化的投資業務。中堂鎮潢涌走的則是一條自辦企業之路,發達的集體經濟造就了中國造紙名村之名。雁田和潢涌在發展過程中,從來不抗拒技術的升級,也不依賴人的數量的擴張,它們的繁榮和發展卻從未中斷。
機器換人不可能一蹴而就
機器不可能完全代替人,東莞機器換人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按照有關部門統計,目前,大朗毛織行業已全部完成第一階段的機器換人。而在周齊眼中,如果說毛紡自動化分三步走,現在大朗只走出第一步。
整個毛紡制造環節主要分為織片、縫盤、后整三大工序,后兩個環節均未能完成自動化。數控織機只解決了織片環節自動化,即將原料織成一片片的材料。以往,織片需要9個工人,那么縫盤就得3個工人,后整再配2個,而現在,織片、縫盤和后整的工人配比是1:3:2.
目前,大朗縫盤工人的月工資已經漲到了6000元,劉傳富原先所在的工廠晶暉針織有限公司老板陳偉光,有時不得不花兩百到三百一天的工資,請劉傳富等人幫忙找臨時工。一次,為趕貨期,他甚至開出了一萬五的月薪來招縫盤工人。
周齊認為,織片、縫盤、后整、質檢、包裝等多個環節,都可以實現智能工廠或無人車間運作,特別是縫盤很有希望機器換人。但目前,全自動的縫盤的機器仍舊太貴且效果不理想,得不到客戶認可。
縫盤機也正在等待著一場國內的技術革命。周齊說。曾經,大朗的數控織機就得益于數控織機的國產化。在2004年后,便宜好用的國產數控織機開始大行其道。這之前,數控織機被德國和日本壟斷,一臺機器需要二三十萬元,企業根本無力承擔。
問題是從2004年國產化以來到現在,數控織機推廣都用了10年,再到整個流水線全自動化,那該多久啊!周齊感嘆。
機器換人不可能一蹴而就,機器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人。比如我們引進了一個項目,叫黃金裝備生產基地,一臺機器,可以代替十幾個人,但最后一個環節還是要人去做。萬卓培說。
東莞市經信局相關負責人坦言,機器換人并非涉及全部企業、所有工序,有不少環節是機器做不了的。東莞還有大量的中小微企業,他們是就業的蓄水池,對于這些企業而言,機器換人還很遙遠,技術紅利替代人口紅利是一個長期過程。
轉型升級的信心
機器換人無疑增強了企業扎根東莞就地轉型升級的信心,為基層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好的條件。
其實,比起機器換人可能帶來的工人減少,基層更應該關注的,是如何讓企業扎根東莞,就地轉型升級。隨著勞動力廉價時代的結束,東莞一些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要么搬遷內地甚至柬埔寨、緬甸,要么轉型升級,例如自動化技術。周齊說。
在大朗毛紡機械行業打拼了十幾年的周齊親眼見證了毛紡產業轉移:新世紀之初,民工荒在珠三角首次出現。一些港臺大廠開始往周邊省份布局,有的內地老板也開始將分廠開回家鄉。一開始還只是廣西、江西、湖南,算是500公里左右,三四個小時的生活圈內,到了2008年后,就開始轉移到1000公里以外的湖北、安徽、河南等地了。
今年6月,東莞市政府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全市機器換人行動計劃。在外界看來,東莞此舉將大大增加企業扎根東莞的信心。現在不是留不留得住人的問題,而是如何讓企業扎根東莞發展的問題。
幾年前,工人一個月連加班才2000多元,現在不加班一般普工起薪都到了3300元左右。每年春節后,陳偉光最頭疼的就是聽到工人跟他討價還價:加300就回來!近三年來,他為此支付工人工資幾乎每年上漲百分之十幾,說到這里,陳偉光愁眉苦臉。現在,類似毛紡行業已經陷入工人青黃不接,年紀大的工人在縫盤時眼花手慢,而90后并不愿意進入這一行當。
唯美陶瓷相關人士則感到很慶幸,他們早就實現了自動化生產。現在,一些勞動強度高的崗位,工資開到七八千多都鮮有年輕人愿意做,但這一招工難題并沒有給唯美造成太大的困擾。
有些產業,如果再不上機器的話,你說還有什么競爭優勢?你除了提高人工工資,還有什么手段能吸引人家過來?面對市場消費的多元化發展,設計上很復雜,工藝上也很復雜,用人做不了的時候,就要用機器去做。萬卓培說。
周齊說得更為直接:不管你習不習慣、愿不愿意,隨著自動化設備價格下降,人工成本上升,二者總會讓企業越來越傾向于機器換人,這是歷史潮流。他伸出雙手,將一手往下壓,一手夸張地往上抬高。
學者們也早就看出了這一點。你不要抱怨工人難招,中國工人已經被廉價地使用了這么多年,現在只不過是人口紅利宣告結束。近日,在莞商學院一周年論壇上,獨立經濟學家金巖石告誡臺下企業家,在高速發展了30多年后,有些趨勢企業必須學會接受。
他認為,流動人口大量集中于制造加工、餐飲服務等附加值較低的產業末端,無法成為未來東莞大城市人口集聚的主干。城市化需要的高層次、高技能人才比例過低,又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新一輪工業化。因此,有必要使換下來的工人加速成長為知識型生產者,奠定大城市人口基石,讓機器換人成為倒逼東莞產業和社會轉型的一個契機。
機器換人配套政策
機器換人過程中,政府還應運用好和完善配套政策,進一步激發基層創新、創業、創富的激情,破除路徑依賴,助推東莞成功轉型升級。東莞市機器人技術協會副會長羅百輝認為,部分基層干部群眾對機器換人的擔憂,歸根結底還是源于對租賃經濟的路徑依賴。發達的村組經濟,曾是東莞最耀眼的名片。但輝煌的過去,形成的路徑依賴,成為東莞村組經濟轉型升級的思維障礙。事實上,早在東莞吹響機器換人的號角之前,人口紅利已經在逐步喪失,租賃經濟早已難以為繼。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,東莞已經嘗過了租賃經濟帶來的苦頭,村組經濟轉型早已時不我待。
今年6月5日,市委書記、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徐建華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:機器換人后,工業吸納就業能力下降,隨著工人的減少,可能對一些村組和村民的租賃收入產生影響。這種影響屬于轉型升級過程中的陣痛。長痛不如短痛,我們既不能因為有陣痛就停滯不前,同時也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減少、舒緩陣痛。
羅百輝指出,機器換人是東莞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。機器換人將促進產業升級和人的升級,從而推動東莞整個城市的升級。在這個過程中,基層也將享受到東莞轉型升級帶來的紅利,而不僅僅是已然式微的人口紅利了。在這個過程中,伴生的社會問題需要未雨綢繆。政府在大力推動機器換人的同時,還要運用好和完善配套政策,進一步激發基層創新、創業、創富的激情,破除路徑依賴,助推東莞成功轉型升級。